燃爆了(崔子恩现状)崔子恩性别,二十世纪中国小说批判之六:崔子恩的实验文本,山海经 崔子恩,
当我们的想像力和感悟性在时下各种时尚文本、灌水般的网络文学的包围之中以及既定的阅读习惯里日趋麻木、迟钝时,有一种无从界定、富于原创性的文本却以它奇魅诡异的风格、大胆而睿智的力量刺砭你的神经。面对它,你显然感受着一种触目惊心的震颤性的阅读体验,这种阅读经验让你感到了刺目的新鲜,有一种成都麻辣火锅的味道。你终于闻到了久违的先锋气息,这种气息弥漫在渴望创新的俗世之中,如美人一笑,黯然消魂。这种文本迎合了博尔赫斯的说法:“我不为任何人写作,我写作是因为我觉得需要写作,并没有想到读者。”没有顾及读者的写作,直接踏入写作的深渊,这才是真正的写作。远离世俗,独守一隅。
在当今消费主义写作时代的背景下,崔子恩是为数不多坚持纯艺术写作的作家之一。翻开他的“实验文本”——长篇小说《丑角登场》与《玫瑰床榻》,让人明显感受到一种阅读的冲击,它们无疑是当代中国文学中的异类,也是堪称“奇书”的文本。《丑角登场》是对性别进行多维书写的小说,其中有惊世骇俗的寓言化故事,在崭新的文本空间多重交织关于器官政治、性别学说的主题,让人在阅读中感受惊心动魄的震颤体验。而《玫瑰床榻》则是一部混淆小说与戏剧文本,独创游戏主义哲学理念的小说。犀透的思想锋芒,恣肆纵横的叙述策略,颠覆解构旧有的一切,深化小说文本的解放,如同一次文字的哗变。
事实上,实验文本以其自身的独特性傲立于众多的普通文本之中,可以说实验文本是写作中的写作。文字还是平常的文字,但意思却变了许多,它让你对阅读产生一种畏惧以及探案般的好奇之心。正如罗马尼亚作家埃·米·齐奥朗所说的那样:“写作是释放自己的懊悔和积怨,倾吐自己的秘密。” 我们知道《丑角登场》与《玫瑰床榻》的作者是一位同性恋作家,这种身份无疑会带给他的作品一些或大或小的影响。罗兰·巴特在《写作的零度》一文中曾经说过:一位作家的各种可能的写作,是在历史和传统的压力下被确定的。可能,冒犯之美就此产生。
专栏作家苏七七曾经说过:从一个读者的角度看,崔子恩的小说是个奇怪的文字城堡。又纯洁,又放荡,又柔弱,又放纵。有些人读人要爱惜他,有些人读人要诅咒,可是这些,又有什么关系?他的小说为自己而写。“谈话是一种交流,讲课是一种交流,拍电影是一种交流,惟独写作不是,尤其写小说不是。与交流、与他人无关的事,我做起来最放松最没有压力,最得心应手,因为它无需任何顾虑和责任,包括自己对自己。写小说仅仅是一种写作游戏,类似于一个孩子独自在家,独自玩搭积木,独自吮手指,独自跳来跳去,独自玩弄自己的小鸡鸡,独自唱一些自编自造的歌儿。写小说可以根本不用关心别人是否喜欢,是否赞同,是否感动,是否咒骂或推崇。因为,没有别人。” 所以崔子恩象一个任性的孩子,夜里一个人在海边堆沙堡一样,筑起他的文字的伊索城。
从某种意义上说,小说是作家与世界对话的一种方式。崔子恩以他的“实验文本”向我们展示了写作的另一种空间。“良好的古典文学功底和长期的电影艺术探索,为崔子恩奠定了一个坚实的文化基础,同时也为他提供了无限充裕的建筑材料和十八般武艺集于一身的写作手段。在崭新的文本空间里,崔子恩可以自由无拘、纵横恣肆地解构旧有的一切。奇特的、非常规的文学策略,机智的语言,锐利的思想锋芒以及题材上对性别精妙的多维书写——‘跨性别书写’(女权主义学者戴锦华语),彻底砸开了词语及观念的牢笼。一种隐秘的、非常的现实存在,一种最大限度释放自己想象力的写作的‘可能性’,宛如壁垒后面的神秘领地真正敞现在我们面前。”它让我们惊讶于文字的另一种魅力或者说是魔力。
曾几何时,孙甘露、格非等先锋小说家的写作令文学爱好者望而却步,令各式各样的批评家一筹莫展。如今,崔子恩的《丑角登场》、《玫瑰床榻》以另类的写作全面挑战了文学的观念与形式,电闪雷鸣般震击着我们的阅读惰性。他如此执拗地行走在词语的密林里,对世俗生活不屑一顾,对传统写作的规章制度熟视无睹。进入崔子恩的文本空间,同时也是进行着一次“穿越罗布泊”式的精神历险。即使是失败,也给后来者留下了宝贵的写作经验。先锋性的写作由于其自由精神和反叛姿态,通常对切近的日常生活和日常事件采取了不卷入的态度,它只卷入到自己的想象世界里,那里比日常生活和日常事件有着更大的风暴和更持久的和谐。
秘鲁作家巴尔加斯·略萨曾经说过:“没有一位作家是想到为他的同类,或者是为了使人类生活得更美好而进行写作的。文学对于作家无异于大麻对于一个吸毒者。这并非一种职业,它要比职业更加深刻,更加内在和复杂些。人们总是根据自己,根据个人的问题进行写作的。写作是最具有个体性和自私性的工作。一个人写作是因为他有了切身体验,尤其是有了自己企图解脱的反面经验。”崔子恩的小说可作如是观。而罗伯·格里耶则说:“小说家创作小说,小说也要‘创作’自己的读者。读者跟作品的关系不是理解与不理解的关系,而是读者参加创作实验的关系。” 崔子恩的作品可以说是法国新小说派作品在中国的传人,其读者也不是传统的了解故事的那种,而是参与创作实验的新型读者,这样的读者其实是小说的另一个创作者。然而这样的读者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培养出来的。
说到崔子恩的小说,不可回避他的同性恋的身份。事实上,这种身份在很大的程度里影响着他的书写。“我时常模糊了泪眼,望向我的家园。我用一种本能的方式,拒绝做一粒种子。我耽于童年复活的幻觉。我担心,倘若有一天我的童年复活而归,向耶稣复活来见他的弟子,而我已有了后代,只好由后带来接续那份童年。我耽溺于这种情结,并为此注定成为终生没有后代的人。”后来在一次采访中,崔子恩坦率地说:“我的小说大部分是破坏‘一对一’的感情模式,或者说,我不想让所谓‘一对一’感情形成指标。”对此,诗人、作家鲁羊的评价是:“崔子恩的作品看起来有点疯魔放荡,实际上呢,整个儿一唯美。而且还是当今小说中罕见的唯美主义,不可救药,彻头彻尾。”
2001年,崔子恩的小说《舅舅的人间烟火》获得了“德国之声文学大奖”,并应邀赴科隆领奖。评委对《舅舅的人间烟火》是如此评价的:“优美神妙的笔触,描摹出一种不被社会接纳的人物,对其生活感人而坦荡的承担。” 《舅舅的人间烟火》,可以说是崔子恩带有自传色彩的人生经历的片段集锦。带着不可思议的唯美走向深渊,奸情如焰火,同性如手足,展现了另一种人生的际遇,流淌着同性恋者人生的压抑、孱弱、渴望和心酸。正如我的“舅舅”——“舅舅”是一个颠覆了传统中的男性形象的人物,他美丽清秀,遗世独立,吸引着三角城里众人的目光。“他生来面若桃花,甚至呼吐出的气息都带有一股奶与花蜜混合的香甜。”
《红桃A吹响号角》可以说是崔子恩的唯美主义巅峰之作,既有《舅舅的人间烟火》般的唯美与感伤,又有伪科幻故事的想象力;小说的文字像丝绸一样光滑而美丽,描绘着如同精美的刺绣一般繁华而绚丽的场景与意象。通过强有力的文字书写,向我们展现了同性恋之美。事实上不管从哪些方面来说,不管人们是否有足够的耐心,都有必要读一读崔子恩的小说。否则,人们不能说领略到当代中国小说的最险峻的风光。崔子恩的小说,绝不仅仅只是一个最著名的同性恋者写的关于同性恋的故事。崔子恩小说散发出的汉语的文字清香,以及文学意象的个性魅力,足以让他跻身于屈指可数的当代最优秀小说家之列。
本文系作者 @河马 原创发布在河马博客站点。未经许可,禁止转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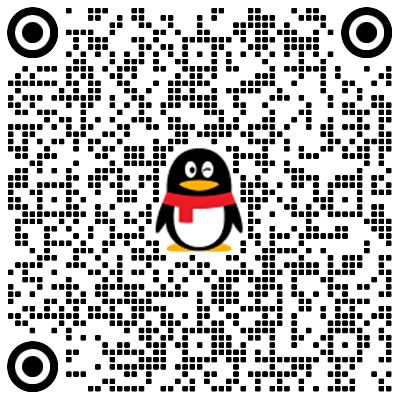
暂无评论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