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货分享(难以想象的画面)你难以想象,难以想象的时间之触动,德州平原县市民讲述地震时刻,
乔纳森·明格尔(Jonathan Mingle)
《这是钱斯!:阿拉斯加大地震,吉妮·钱斯和她维系在一起的破碎的城市》
作者:乔恩·穆阿勒姆(Jon Mooallem)。
兰登书屋, 315页,18美元(平装本)
《不整合之书:对逝去时间的思索》
作者:休·莱佛士(Hugh Raffles)。
万神殿出版社,374页,30美元
1964年3月27日下午晚些时候,阿拉斯加安克雷奇的社区剧团的成员们,正在准备当晚演出《我们的城市》,这是桑顿·怀尔德(Thornton Wilder)1938年的剧本,表面上讲的是20世纪初美国的小镇生活,但用一位评论家的话来说,是关于“人类如何面对巨大的灾难。”与此同时,他们的邻居们正在打烊,做晚饭,或者在复活节周末回家前喝杯啤酒。下午5点半刚过,吉妮·钱斯(Genie Chance)开车送儿子去市中心办事,突然车开始猛烈颠簸。起初她以为车胎瘪了。然后她注意到建筑物在摇晃,道路在起伏,她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地震持续了近五分钟。地震停了之后,钱斯把儿子送到了他们家(幸运的是家完好无损),然后赶到了安克雷奇的主要商业大道第四大道。 她发现整条街的一边都比另一边低了十英尺。顾客们迷迷糊糊地从凹陷的酒吧里走出来,抬起头来。半个小时后,太阳落山,大雪纷飞,安克雷奇的10万居民不知道损失有多严重,也不知道有多少人死亡。电线断了,大部分电话也中断了。但肯尼电台仍在广播,由一台发电机提供动力。
在接下来的30个小时里,钱斯,阿拉斯加州第一位女新闻播音员,通过肯尼电台的广播,向她的城市讲述了这场危机。她成为了事实上的公共安全官员,让听众知道哪些道路被封锁了, 哪些地方着火了,哪些地方有临时庇护所和急救站。她告诉他们,医院需要熟石膏、电工和水管工。在短暂小睡之后,钱斯一直播报到复活节早晨。她大声朗读那些寻找失踪亲人的人的信息,以及那些想让家人知道他们安然无恙的人的信息。一个男人后来把她通过他的晶体管收音机发出的声音描述为“我们恐怖的夜晚中唯一的灯塔”。
钱斯是如何将年轻的、支离破碎的边境城市安克雷奇联系在一起的,这是乔恩·穆阿勒姆的《这是钱斯!》中的核心叙事,是对一场大多被遗忘的灾难的精心报道。9.2级的阿拉斯加大地震是北美有记录以来最强的地震,也是世界上有记录以来最强的地震。安克雷奇有9人遇难;至少有131人死于这次地震,其中大多数死于太平洋沿岸的海啸。
穆阿勒姆解释说,安克雷奇的死亡人数之所以如此之低,部分原因在于,几乎所有的伤者都在周五夜幕降临前被“非官方的急救人员” 从废墟中救出:“在安克雷奇的每一个地方,成群的普通人都立即自发地去工作,像一种公民的免疫反应一样合作起来。” 一位举止温和的心理学教授和当地一所大学的业余登山者领导了搜救工作。 旁观者用自己的拖车和千斤顶,将市中心部分倒塌的彭尼公司大楼的废墟和机场倒塌的控制塔进行拆分,迅速救出幸存者。
这些花絮给人的印象是《这是钱斯!》是另一篇关于在灾难中生存的人们之间萌发的团结的文献。* 穆阿勒姆对恩里科•夸兰泰利(Enrico Quarantelli)的研究也能起到同样的作用。夸兰泰利是一位年轻的社会学家,在地震发生后的那个周日,他和一些同事飞到安克雷奇, 采访市政府官员、应急人员和街头民众,这是他们对灾难心理反应的新兴研究的一部分。夸兰泰利是灾难研究学术领域的先驱,他记录了在不同文化和地理环境下,在面临灾难的情况下,人们几乎总是会发现并挖掘出同胞感情和无私的深流。
但有早期迹象表明,穆阿勒姆真正的研究对象在别处。在书的前几页,他反思了灾难给我们的时间感带来的“可怕的魔力”,“当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世界瞬间改变;当现实突然被颠覆,难以想象的事情淹没了现实生活。”
“灾难导致人们将注意力集中在当下,” 夸兰泰利和另一位合著者在1975年写道。这种兴奋(很多人在他们突然团结起来的经历中发现了这一点)来自于他们在时间之外站在一起的感觉:"从当下的现实情况来判断,对过去和未来的担忧是不现实的。"
灾难不仅将沉积物层、构造板块的边缘、建筑物和巨石搅在一起,还将个体生命搅在一起。它们消除了那些让人欣慰和不安的错觉——那些认为明天会和今天一样,认为我们脚下的土地是稳定的,认为我们是独自挣扎的。它们提醒我们,不稳定、破裂和动荡是世界的默认设置, 我们在共同的不稳定中始终团结在一起。50年后,一位地震幸存者告诉穆阿勒姆:“即使是现在,我也能从窗外看到这片坚硬的土地,知道它不是永久的。它可以随时改变。它在运动。一切都在运动。”
2005年,一场地震把沉睡在东京一家酒店的休•莱佛士从睡梦中惊醒。他看到街对面办公楼里的工作人员伸出胳膊,“寻找平衡”,然后发现他也摆出了同样的姿势。他意识到,他和办公室工作人员是生活在另一个维度的同伴,“都生活在一个不稳定而亲密的能量空间里。”
“在那个空间里,时间也发生了一些事情,”他在《不整合之书》中写道。《不整合之书》是一部迷人的、融合了历史、回忆录、人类学、旅行和时间旅行的作品。
它破裂,断裂,分裂。类似的事情经常发生在高度危险的时刻:当你的汽车失控时,当你从自行车上摔下来时,当你意外地收到一个亲密朋友或亲戚去世的消息时,当你拉开窗帘,毫无疑问地看到红色的熔岩喷泉从地球上喷涌而出时。时间中断了,它在英语单词的两种意义上悬空了:放慢到几乎为零,让你实际悬空,就像从液体中旋转出来的微粒,不再接地气,因为地面不再是地面,不再平衡,因为不再有一个空间矩阵让你的感官定位。
灾难打破了我们认为时间是线性过程的假设。当地震、海啸或火车脱轨时,正常时间被揭示为“时间暂停了,我们用来保证日常安全的脆弱时间,但它总是在等待,总是准备被炸开。”
从莱佛士书中的第一句话,我们知道,20世纪90年代中期,他的妹妹弗兰基(Franki)在苏格兰生双胞胎时去世,不到三个月后,他的妹妹莎莉(Sally)在伦敦郊外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悲伤让他迷失了方向,他开始寻找可以依靠的东西:“我开始寻找岩石、石头和其他看似坚固的物体,在这个失去锚定的世界里充当锚。”
《不整合之书》记录了他数十年来从石头中寻找理智和慰藉的过程。莱佛士是新学院的人类学教授,他在北大西洋旅行,到冰岛、奥克尼群岛、斯瓦尔巴特群岛、格陵兰岛,以及他的家乡曼哈顿岛的边缘。在冰岛一个偏远的海滩上,莱佛士拿起一块光滑的、长方形的玄武岩,这块玄武岩是七千年前从流动的熔岩中形成的,他想象着它“在我91号街的窗边打磨得锃亮的木架上,旁边是来自其他地方的石头,与其说是世界地图,不如说是世界本身。”
这就是他所追求的:岩石的存在性,岩石存在带来的稳定压力。但他发现的不是答案和锚,而是深不可测的谜。他所着迷的石头——无论是布朗克斯与曼哈顿交错的神秘的、半浸没的大理石纹理,还是丹麦自然历史博物馆庭院里一块重达20吨的陨石——都代表着消失了的世界。在他永不满足的好奇心中,片麻岩、砂岩、大理石、白云母和铁的碎片成为了催化剂,促使他思考那些可能曾经接触过他们的人。无论他走到哪里,他都在梳理这段时间漫长的滑坡留下的残骸,并把过去生命的闪光残余拉出来。
在苏格兰北端的奥克尼主岛,莱佛士参观了一簇优雅的砂岩板,它们被称为“斯坦尼斯站立石”(Standing Stones of Stenness),曾经是熙熙攘攘的新石器时代建筑群的中心。几千年来,其中的奥丁石高八英尺,中间有一个对称的椭圆形开口,吸引着人们举行仪式,承诺健康,生育和忠诚。情侣们会对着它发誓,通过这个洞交换硬币,或紧握双手。
二十世纪的宗教学者米尔恰·埃利亚德(Mircea Eliade)认为,像这样的石头是他所谓的“象形物”(hierophanies)的例子,这些物体作为那个时间(那个时代) 的入口,这个神圣的平面独立于历史上的时间进程,是时间之外的时间。对于奥克尼岛的人们来说,奥丁石就是这样一个大门,直到威廉-麦凯上尉(Captain William MacKay),一个被游客和信徒在他的田野上践踏所激怒的佃农,在1814年把它炸成碎片。其它几座巨石仍然矗立在一个海湾上方的被风吹过的平原上,在那里它们对莱佛士这样的游客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
在六月的一个刮风的日子里,他爬上了一个古老的山顶采石场,五千年前,那里的石匠们开采出了砂岩。当他试图“想象泥瓦匠们通过奥丁之石上那个消失已久的洞,及时地砸开了一扇窗户” 时,他遇到了一个滋养人心的僵局:“这种不可能知道的事情让我莫名地感到幸福。”
对过去的根本不可知的认识是莱佛士项目的核心:“有时差距太大,人、动物、物体、世界都消失了,对我们仅有的一点时间来说,时间太多了。” 后来,他解释说,根据地质学家的说法,不整合面是沉积物沉积的不连续点,在这里,来自不同年代的两块岩石,其来源可能相差数亿年,直接接触在一起。 不整合面表示嵌在地层中的记录中有一个缺口,这是地质记录跳跃的地方。
在这种情况下,不整合接触“既是一个接缝,也是一个断裂:一种并列,揭示了一个无法弥合的裂缝,” 莱佛士写道。而且生活,
充满了不整合——揭示了时间上的空洞,也是情感、知识和理解上的裂缝;这些漏洞无情地吸引着人类的研究和想象,但却拒绝以我们可能希望或认为需要的方式,来顺应、愈合或服从解释。
尽管这一切都很棘手,莱佛士还是忍不住一次又一次地想象自己如何进入那个缺口。就像地质学家用放大镜从几亿年前的沉积层中取出单个颗粒一样,他有一种特殊的天赋,可以为他的人物创作特写镜头,使那些失散已久的人感觉眼前一现,仿佛那些古老的采石场工人正从我们身边艰难地走过,一边咒骂着,一边咕哝着。
莱佛士的题词借用了罗伯托•波拉尼奥(Roberto Bolano)的小说《遥远的星星》中的一句话:“……仿佛时间不是一条河流,而是一场正在附近发生的地震。” 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想法:如果时间的毁灭像地震一样以一种不可避免的力量迫使我们注意,那会怎样? 如果时间不是被体验为一种流动,而是被体验为一种现象,它的能量战胜了你,让你感到恐惧,迫使你伸出手去寻找平衡,那会怎样?
这个前提激发了《不整合之书》中记录的流浪,这本书既不是回忆录,也不是对悲伤的沉思: 莱佛士的两个妹妹只被提到了几次,而他自己的精神状态只有在必要时才会被仔细审视, 以分析他从地球深处的过去所接收到的特定信号。相反,他带领我们穿越尘封的档案、被遗忘的日记和模糊的照片的那些蛀孔。 他邀请我们和他一起思考很久以前不同世界之间经常发生的暴力冲突。
有些石头成为了剥削和种族灭绝篇章的入口,被贪婪的殖民主义企业和我们的现代采掘型经济所忽视的起源故事。我们瞥见了亨利·哈德逊(Henry Hudson)和他的船员们第一次见面,然后绑架并杀害了一些莱纳普人,他们居住在后来成为曼哈顿的岛上,也瞥见了海盗们把他们的爱尔兰奴隶带到冰岛的新农场。
在北极圈之上的挪威斯瓦尔巴特群岛的斯比次卑尔根岛上,莱佛士创造了“鲸脂石”这个词来描述鲸鱼的痕迹,“溢出的油与沙子、砾石和煤炭一起凝结成一大块岩石”,从17世纪到19世纪,是狩猎队和捕鲸者把斯瓦尔巴群岛的海滩变成了工业规模的加工中心。鲸脂石——“人类地质学的产物”——是人们用来煮鲸脂的铜坩埚的轮廓。莱佛士描述了产生这些幽灵般的残余物的捕鲸机制,并追溯了偏远的斯瓦尔巴特群岛成为“早期现代世界经济” 中心枢纽的更广泛的联系和诱惑。
一块重达20吨、称作阿格帕里克(Agpalilik)的陨石如今坐落在丹麦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庭院里,它将莱佛士带到了格陵兰岛西北部的萨维西维克村。阿格帕里克陨石是约克角流星雨留下的众多铁纹陨石之一,当地因纽特人珍视这些陨石,认为它们是制作刀具、长矛和其他工具的原材料。这些珍贵的岩石在19世纪早期就引起了英国水手的注意。莱佛士从日记和其他资料中重建了他们在1818年第一次与因纽特人相遇时的奇怪和不对称。他还详细地描写了美国极地探险家罗伯特·皮尔里(Robert Peary)对因纽特人的掠取和剥削,包括他在1897年把6个人——1个女人,3个男人,两个孩子带到了纽约(连同3块他卖给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陨石),在那里他们被公开展示,并被当作标本对待。其中四人死在那里。
这些推测性的尝试并不符合传统的叙事弧线。使这本书的咒语列表、时间上的快速浏览和档案研究如此连贯的,是莱佛士对寻找、更近地寻找、再寻找的强烈承诺。这个结果读起来像是几十年压缩的产物,就像他研究的岩石一样。挤压《不整合之书》的力量不是时间和重力,而是同情、悲伤和惊奇。
当然,结构是大多数作家的支柱和救星。相反,莱佛士依靠的是他的注意力的约束力。他追求的“不是一幅世界地图,而是世界本身”,而世界本身只提供了缺口和谜题。他是研究不整合的学者,毕竟那些拼接在一起的区域,无法给出明确的解释,也不易构造。他隐含的前提是,如果不关注这些缺失,我们就无法理解当今世界,无论它的毁灭和丰饶,残酷和安慰。
在他的两个妹妹去世15年后,莱佛士前往外赫布里底群岛,并参观了刘易斯岛卡兰尼什的立石。在离他妹妹弗兰基1970年代居住的房子不远的一座山上,他思考着 "即使是至死不渝的东西也有顽强的生命力",并想知道被称为诺克·图尔萨(Cnoc an Tursa)的巨大片麻岩是否像一些考古学家推测的那样,是古代北大西洋贸易和文化中心卡拉尼什的神圣中心:
另一个世界轴心连接着五千年前的世界和今天一样不可攻破;它坚不可摧,深不可测——但不比我妹妹死后的25年更深不可测。站在时间的边缘,我感到它们在洗刷着我。但愿这个裂口能张开,把我也吞下去。要是我知道规矩就好了。一些脆弱的东西坏了。在这个我都不知道的世界里,有一些确定,一些自信。
穆阿勒姆和莱佛士都在摸索应对灾难的策略,他们的书在寻求平衡时——比如那些东京办公室职员伸开双臂摆出的姿势——而不是叙事——读起来更有价值。但是,莱佛士避开了结构,而穆阿勒姆有一个不同的方法:他借用了他的结构,并将其展示出来。
他的第一段呼应了怀尔德在《我们的城市》中以自我为参照的开篇:“这本书名叫《这是钱斯!》,作者是乔恩·穆阿勒姆,兰登书屋出版,安迪·沃德编辑。” 题词本身来自《我们的城市》;这本书分为三幕;它以一个角色列表开始。在最后一页,它徘徊在安克雷奇的社区戏剧演员,在地震10天后,他们终于为疲惫的邻居上演了他们的表演《我们的城市》。
当穆阿勒姆设定这个场景时,他打断了自己,注意到50年后,扮演韦伯太太(Mrs. Webb)的中学教师将死于心脏手术并发症,而扮演酗酒牧师的年轻艺术总监在穆阿勒姆采访他几个月后将去世。这并不是《这是钱斯!》中的第一件时间旅行作品。在早期,穆阿勒姆讲述了某些人物——吉妮·钱斯在肯尼的同事,阿拉斯加国民警卫队的指挥官——将在未来数周或数十年内遇到麻烦。
在其中有一段很长的片段中,穆阿勒姆以第三人称的形式描述了自己对这本书的叙述,就好像他在叙述灵魂出壳的经历。他描述了自己在翻找一盒盒钱斯的日记和纪念品、采访幸存者时感受到的“莫名的沮丧不安”:“他开始想象自己的盒子。他想象着已经有多少盒子在外面,在别人的地下室里,有多少人根本没有留下盒子。” 人类记录中所有的空白,所有的呼吸不整合,所有失去的时间。
他对主人公们的生活结局有着令人眩晕的了解,这让他不知所措,他终于重新阅读了怀尔德的剧本。(在采访中,穆阿勒姆承认,他在学生时代读《我们的城市》时,觉得它“有点做作”,直到后来为他的书做研究时,他才挖掘它的深度。) 当他读到舞台监督的一句“无所不知的旁白”(“吉布斯夫人首先去世了”) 时,他顿悟道:“那就是我。” 这种顿悟可能听起来像是固定的,有时所有这些自我参照的假动作都感觉有些强迫。但穆阿勒姆的舞台经理设置最终将《这是钱斯!》从单纯的灾难纪实提升为对高阶灾难的凄美沉思。
穆阿勒姆的结论是,等待《我们的城市》中角色,以及安克雷奇镇的人们——所有人——的更大灾难是“不相关的”。在他看来,真正的灾难是时间如何将我们所做的、所热爱的、所建立的和所记录的一切付之一炬。《我们的城市》没有发生地震,但地面仍然在格罗弗角落的居民脚下移动,“以最稳定、最可预测的方式:远离他们,时间向前推移,” 他写道。
这个结论似乎不太正确。当然,时间的洪流无情地,静静地把我们的爱和我们的作品磨成淤泥。但是,怀尔德的戏剧如此震撼人心的真正原因——从高中到百老汇舞台,它仍然是当今最常上演的戏剧之一——并不在于它对人生的微不足道的毁灭性描述。怀尔德希望我们面对的最终灾难不是无关紧要,而是漠不关心。
在戏剧的结尾,艾米丽·吉布斯(Emily Gibbs)回到她的凡人生活从坟墓之外,选择重温她的12岁生日。当艾米丽看着母亲在厨房里忙来忙去,沉浸在早晨的例行公事中时,她第一次看到,她和她的家人以及她的邻居们是如何真实地生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没有完全意识到彼此的存在。“我不能继续了,” 艾米丽喊道。“它走得太快了。我们没有时间对视对方。” 她开始哭泣,因为这场灾难的范围打击了她:“我没有意识到。所以我们从来没有注意到这一切……"
“有没有人在生活的时候意识到生活……每一分钟吗?” 她问舞台监督。“不,” 他回答道,然后停顿了一下,接着补充道,“圣人和诗人,也许他们做了一些。”
近两年来,时间的流逝似乎被疫情大流行扭曲了,在这之后,这一特殊的忽视危机又有了新的意义。新冠肺炎本身就是不一致的,无论是在世界历史上还是在许多个人生活中,它剪断了文明的断层线,在不自在的接触之前和之后留下了断层线。两年没有在一起,当大多数人突然发现他们面临同样的问题:如何处理缺席的东西?
穆阿勒姆根据吉妮·钱斯在地震后几天写的一封信给出了答案,他认为这是她的见解。穆阿勒姆给出的答案也是他这本书的主要论点:“我们对抗混乱的力量是联系。” 但是,当穆阿勒姆在其他地方写道,“横向……就像一张网一样把我们的线盖起来”——看看你身边的人,即使是在疫情大流行期间,你也会找到安慰和联系——莱佛士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维度:遥远的过去。
我们不需要地震就能注意到这个世界是多么的开放。只要四处看看。这里到处都是逝去的东西。我们需要圣人和诗人那样的努力,才能对生活保持警觉,对生活的可能和不可能保持警觉,对我们周围正在发生的奇迹保持警觉,对他人的痛苦保持警觉,更不要说对把我们带到这一关口的交叉道路保持警觉了。但对于我们其他人来说,莱佛士提供了一种模式。
“注意”(attention)这个词来源于拉丁语ad和tendere:“向……靠近”。他说,我们可以尝试的一件事是,及时跨越这些鸿沟,同时明白我们永远无法真正触及另一边。他指出,“地质学,就像考古学一样,有其乌托邦的维度——对缝合时间的承诺。”
单靠关注是无法完全弥合这种裂痕的。尽管如此,莱佛士还是向我们展示了一种伸向空虚的行为——关注“逝去的世界”——即使不能给我们带来悲伤真正的慰藉或安慰,至少也能让我们稳定下来。当他试图描绘那些新石器时代的泥瓦匠凿奥丁石的场景时,其效果就像透过东京办公室的窗户看到地震中期,看到自己笨拙的、真实的寻求平衡的镜像回来。当世界崩塌的时候,你会伸出手去抓住某物或某个人。提醒一下,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一直在以这种方式伸出手来——试图敲开“一扇及时的窗户”,不是为了闹着玩,而是为了满足人类深刻的需求——这是很有用的。
我们有足够的能力向后延伸。用你的手在10代或100代人以前用过的磨石上摩擦,在那一刻,你进入了穿越时间鸿沟的电弧,并获得了一种更大的共同努力的感觉,它不会抹去自我,而是更充分地放置自我。距离拉近了,即使只是一点点。
在《不整合之书》中,这种持续的努力展现了一种短暂的灾难反应,类似于安克雷奇市民的公民免疫反应,将遥远而迥异的生活编织成一个充满苦难、掠夺和匮乏、生存、光明、坚持和勇气的共同故事。不是许多故事,而是整个故事。
在《不整合之书》的结尾,莱佛士引用了人类学家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的一段话:
当奇迹发生时,就像有时会发生的那样,在隐藏的裂缝的一边和另一边,突然发现两种不同种类的绿色植物紧挨在一起,同时,在岩石中可以看到两种不规则复杂缠绕的菊石,于是,以自己的方式证明了几万年的空隙,时空突然合二为一;当下鲜活的多样性使时代并置并延续。思想和情感进入了一个新的维度,我感到自己沉浸在一种更密集的可理解性中,在这种可理解性中,几个世纪和距离相互回答,最后用同一个声音说话。
“沉浸在一种更密集的可理解性中”:这是一种恰当的方式,既能捕捉阅读莱佛士杰出作品的体验,也能捕捉他的成就的范围。如果时间是发生在附近的一场地震,莱佛士就是那场灾难的吉尼·钱斯,他放大了交错的声音,微弱的回声——其中许多声音被历史的守门人所忽视或轻视——穿越荒凉的大草原,通过他选择的石头的晶体管收音机锻造出一种亲缘关系。在他的探索过程中,他满怀同情地跨越地质年代和个体生命的不连续点,莱佛士给了我们一种声音,这种声音可以在一段时间内将一切团结在一起。
*这一流派中最好的作品或许是丽贝卡•索尔尼特(Rebecca Solnit)的《地狱制造的天堂》(维京出版社, 2009),它优雅而深入地捕捉了灾难幸存者中出现的那种愉悦的、乌托邦式的社区意识。
《纽约书评》2022/02/10
本文系作者 @河马 原创发布在河马博客站点。未经许可,禁止转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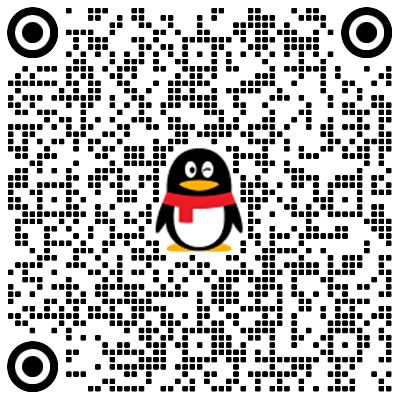
暂无评论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