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满干货(残奥会精神英语介绍)残奥会精神英文,我们认知的残奥会:重塑社会观的一堂课,张帅对手托特道歉愿坐下来谈,
看竞技比赛的人有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当我们谈论体育比赛时,自然想到奥运会、世界杯(国际足联世界杯)、温网(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NBA(美国职业篮球联赛)……这些当今世界上具有影响力的体育赛事,比赛期间总会被簇拥者们捧为最炽热、鼎盛的时段。其中,奥运会因其集结各类运动项目的综合性、4年的周期跨度以及奥林匹克庆典的仪式感,成为世界上影响力最大的体育盛会。
即便因为疫情全球蔓延,推迟一年的东京奥运会,依然有33个大项、339个小项的赛事设定。为了吸引年轻人的关注,滑板、冲浪、竞技攀岩、棒垒球和空手道成为东京奥运会的新增项目。2014年12月通过的《奥林匹克2020议程》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要增加对年轻观众的吸引力。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表示:“不能指望他们找上门来,我们必须主动作为。”
与奥运会为吸引年轻人做出的改变相比,残奥会依然在为获得更多关注而努力。与此同时,中国的残奥健儿们已经在残奥会的奖牌榜上连续5届实现金牌榜、奖牌榜第一。尤其是里约残奥会,中国残疾人体育代表团获得自1984年参加残奥会以来的最好成绩,107金、81银、51铜,总奖牌数239枚,打破24项世界纪录。不可否认,由于残疾人自身的局限性,比赛或许达不到健全人比赛的激烈和刺激,与体育运动表达力与美的印象也相去甚远,但奥运会传递的一系列价值:和平、参与、公平、挑战自我、追求卓越等,残奥会同样具备。
“残奥会之父”路德维希·古特曼在1953年斯托克·曼德维尔运动会上讲话,在那之后,路德维希·古特曼致力于向欧洲各地推广这一赛事,号召残疾人来参与比赛。
最初以康复为目的的体育运动
1960年至今,已经举办16届的残奥会让越来越多人看到残疾人实现自身价值的可能,也延伸出更多意义。然而,残疾人开始奥林匹克体育运动的起源,却是针对脊髓损伤患者的康复治疗。
二战时,德国医生路德维希·古特曼接受英国政府的请求,在距离伦敦不远的斯托克·曼德维尔的医院创建了脊髓损伤中心并担任主任。被送来治疗的都是残疾军人,为让这些曾经的英雄尽早康复,重新融入社会,古特曼开始研究脊髓损伤的病症。过去对于脊髓损伤病人的一般治疗,排斥一切形式的运动,而古特曼坚信,有效的物理治疗加上病人的健身,能更快恢复其独立性。于是,古特曼要求受伤的士兵即使在病床上也要坚持体育锻炼,办法就是要求病人向上抛掷药丸。
射箭也成了物理治疗的有益补充,它加强了上肢和身体的肌肉系统,有利于呼吸系统和心血管功能恢复。古特曼还发展出一种特殊形式的残疾人运动——轮椅马球,后来为了减小危险,改为轮椅篮球。运动第一次被作为脊髓损伤患者的康复方式。
1948年7月28日,第14届奥运会开幕,来自59个国家的4062名运动员在伦敦相聚。就在同一天,宁静的斯托克·曼德维尔乡间医院草坪上,一场专为脊髓损伤的老兵组织的射箭比赛拉开帷幕。14名男性和2名女性截瘫患者参加了这次比赛。这场由古特曼组织的轮椅射箭比赛,也被视为国际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开端。
直到1960年,在古特曼医生和意大利的安东尼娅·马里奥教授为期两年的精心组织策划下,斯托克·曼德维尔运动会移师意大利罗马。这届运动会安排在第17届罗马奥运会结束两周后,不论从规模还是组织运行模式来看,都初显残疾人奥运会的雏形,来自23个国家的400余名使用轮椅的运动员参加了8个项目的竞赛。在残奥会的历史上,这场运动会被视为第1届残奥会,古特曼也被公认为是“现代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之父”。
体育运动对残疾人而言,本身就是一种挑战,以康复为目的的体育运动,产生的效果远不只是康复。残奥会的举办,让每一位运动员在这片崭新的天地,不断突破着身体的局限和心理的障碍,夺金是每一位残奥运动员的目标,却不是终极目标。
扩展对身体认知的界限
在多数人的观念里,残疾人体育运动多少有些残酷。失去双臂的人奋力游泳,以头触壁结束比赛;视力残疾的人,却要朝着看不见的方向跳远;没有双腿、坐着轮椅的运动员依然要激烈抢拼……“满眼都是挣扎的躯体,扭曲着,蹒跚着,不想看。”旁观者的不忍心出于善意,却忽略了残疾人体育竞技本身的震撼。2012年伦敦残奥会男子100米T46级比赛,无臂选手赵旭以11秒05摘金,比赛前,他在跑道上对靠近它的镜头喊出——“我要飞”;2012年伦敦残奥会,美国选手马特用他的双脚拉弓射出37个十环,夺得银牌,他曾说,如果人生可以重新来过,我希望我还是现在这个样子;2016年里约残奥会上,中国单腿骑士梁桂华战胜拥有双腿的对手,勇夺金牌,他说:“即使只有一条腿,我也能撑起完整的世界。”
根据残疾人田径比赛规定,盲人运动员参赛要通过领跑员协助完成。从2013年,徐冬林成为刘翠青的领跑员,两人的配合至今已有8年。8年间,两人就靠着一条10厘米的牵引绳并肩作战。
残疾人运动员虽然有身体缺陷,但在某些运动能力方面,依然有超乎常人的水平。比如,南非截肢游泳运动员娜塔莉·杜·托特,在2008年获得了北京奥运会的参赛资格,与健全人同场竞技 ,在女子10公里公开水域游泳比赛中,她用一条腿游完全程。残疾人运动员同样可以呈现精彩的比赛,他们需要的不是怜悯,而是平视的眼光和平等的尊重。
美国著名摄影家、艺术家芭芭拉·克鲁格曾有过一个标语式的作品,仅有一行字:身体是一个战场。意为身体是各种力可以在上面驰骋的领域,身体可以引发竞技,可以被重塑。如果身体还是一个机器的话,那它是一个可以被损坏、被修理,进行新的组织和装配的身体机器。从某种程度上说,残疾人的生命形态即使因为种种意外被破坏、重组,但依然能够运转。赛场上,残疾人运动员的每一次挑战都是一种自我创造和发现,扩展了我们对身体认知的界限。
为了更包容的社会
8月24日,东京残奥会开幕式上,国际残奥委会主席安德鲁·帕森斯致辞时称,残奥会是一个平台,但每4年一次是不够的。在他看来,每个人都有责任每天发挥自己的作用,在各自的国家、城市和社区为残疾人建设一个更具包容性的社会。
东京奥运会现场没有观众,但残奥会有。东京残奥组委组织了大约13万名学生到现场给残疾人运动员助威。这显然不是一个观赛举措,而是教育举措。相关官员称:“这个计划绝对可以向年轻一代传授残奥会的价值。”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发起人顾拜旦在第一部现代奥林匹克宪章中写下了提倡“重在参与”的“法则”,“每一个人都应享有从事体育运动的可能性,而不受任何形式的歧视,并体现相互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的奥林匹克精神。”即便是不健全的肢体,依然可以享受运动。
残奥会并不是残疾人的一场“内部聚会”,而是给全人类,特别是健全人上的一堂人生必修课。
回看2008年北京残奥会,它留给中国的不仅仅是感动,更实在的是让普通老百姓在电视上,在大街上,在商场里史无前例地见到这么多“各式各样”的残疾人。“原来中国有这么多残疾人啊!”“残疾人也挺乐观的!”这样的印象潜移默化地在更多人心里树立起一种多元化的社会观。
8月25日东京残奥会赛场,坐在轮椅上的李豪获得男子佩剑个人A级金牌,为中国代表团摘得首金。国内社交平台上,不再同以往般“查无残奥”,官方媒体、普通网友们纷纷为李豪点赞,相关话题也冲上热搜。变化是可喜的,残奥会正在以某种难能可贵的方式改变人们的观念。
联合国数据统计,残疾人占世界总人口的15%。残奥会官方解读这15%的内涵:他们是人类多样性的一部分,是生活在我们身边的普通人。只有更多人了解残疾人的价值,他们才能获得更多机会。残奥会带来的更深层的影响——是让我们摒除偏见、敞开心扉,创造更包容的社会。
来源丨中国残疾人杂志社(ID:zgcjrzzs)
文|王雨萌
编辑丨张帅
★转载请注明来源
本文系作者 @河马 原创发布在河马博客站点。未经许可,禁止转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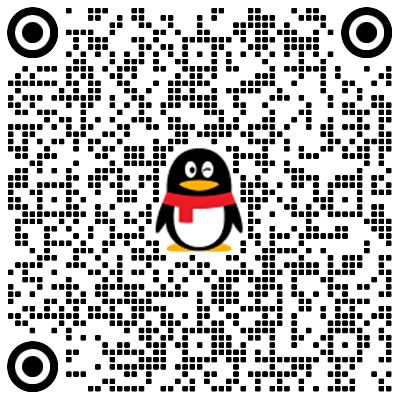
暂无评论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