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看后悔(社交恐惧症怎么自治)社交恐惧症自救指南,社交恐惧症——自负:天生我才,打羽毛球的单机游戏,
自负:天生我才
“尽管神经症患者竭尽全力使自己完美,尽管他相信自己已经达到了完美的境地,可是他并不能够得到他最需要的东西,即自信和自尊。即使他在他的想象中像天神一样,可是他仍然缺乏人间普通牧童的自信心。他可能达到的崇高地位,他可能获得名望,只会使他傲慢自大,但不会给他带来内心的安全感。他内心中仍然感到不为人们所需要,感到易于受到伤害,因此需要不断地证明自己的价值。只要他能行使权利,施加影响,并有赞扬和尊敬来支持他,他就可能感到自己强大而重要。但只要在陌生的环境中并缺乏必要的支持时,只要当他遭到失败或一个人独处时,所有这些洋洋自得的感觉就会很容易地消失殆尽。他那天上的王国经不起外界的干扰”——卡伦.霍妮
由于一个孩子在不利的环境中长大,因此他就不能正确地看待自己,而又因为他的内心缺乏爱与接纳,并活在一个竞争和比较的世界之中,所以他就必须让自己强大到超越他所面临的困境。他会对那些被社会主流价值所推崇的成就与荣誉特别着迷;也会对完美的自我形象极其渴望;同时也试图维系人际的和谐与高尚的品德,只因这样才能增强他内心中的安全感。
这一切的开始仅仅是一些无害的幻想,他会幻想自己成为不凡的人,但慢慢地他把幻想当成了现实,把期待当成了应该,结果他就越来越无法区分想象与现实的距离;他越来越把自己当成自己头脑中所幻想的那个人。最后,他就认为自己就是一个伟人、天才、圣人,反正他已经不再是当初那个无能、被嫌弃、软弱可欺的自己。
在人生的某些阶段,他也许会取得一定的成绩,超越身边的人,接着他会更加坚信“天生我才”,就算日后“光环”已不再,他依然不愿承认自己的平凡。正如,一位女性患者告诉我:我的人生不能和身边的妇女一样的平凡。虽然她在生活中并没有取得超凡的成就,但她却固执地认为自己就应该与众不同。当然,她的痛苦也正是来自于,无论她怎样要求,无论怎样努力,她依然无法摆脱这平凡躯壳。
“不平凡”,成了他人生的追求与对自我的认同,但这一切就好像是“修图”一般——对自己“美丽”的地方无限放大化,对自己的“丑陋”极力地掩饰。所以,他看到的已经不再是真实的自己。因为他已经沉浸在完美的幻想之中,所以他就应该完美无缺,不能有任何缺点,他也必然拥有圣人般的品行与价值观,别人也要以他为中心。任何没有达到他内心指令的地方都会被他认为“不应该”。
因此,我们也可以更好地理解社交恐惧症患者为何会如此痛苦。毕竟他不应该有缺点,不应该被否定,不应该比别人差,不应该是现在的样子。他应该是无可挑剔,完美无缺的。因此他会对任何否定与不足耿耿于怀,比如,脸红或豆豆、甚至是自己脸上细小的伤痕,他也会对别人的不敬而耿耿于怀,因为他应该受到所有人的尊重。如果不能做到最好,他就会逃避现实以维系自尊。
理想化的自我与现实的自我是他内心冲突的关键。毕竟,现实中的自己没有特权,没有受到所有人的敬仰和膜拜,没有圣人般的品质,也不能去掉令人厌烦的症状(在患者眼里任何会有碍他完美形象或遭致别人反感的东西都是症状),但他认为这一切不应该是这个样子,他不应该是现在的自己,他应该成为一个更优秀的人,成为超凡的人物。
当一切顺利,当他活在虚荣之中,甚至是想象中的成就的时候,他极其容易膨胀,有一种君临天下的感觉,俯视芸芸众生。就如同一位女性患者走在街上都会认为周围的人都在关注自己,自己就如同女王一般地存在;而另一位男性患者认为自己就是一个天才,应该懂得一切,知晓所有。当然,此种膨胀他更多的时候会隐藏在内心深处,因为他还应该具有圣人般地完美品德,自我膨胀和吹捧会破坏他如此完美的形象。他就好像特工一样维系着双面的人生,因此,他也注定是一个不真实的人。
虽然,他会把自负当成自信,但他的“自信”却特别的脆弱,一阵风就可能会刮倒。但来治疗的时候,他依然希望治疗师可以帮他找回当初的“自信”,希望治疗师可以给予他“正能量”。他对“自信”有一种偏执的狂热,就算有时他也会怀疑这到底是一种自信,还是一种膨胀抑或是自恋,但一会功夫他就会把这种怀疑抛到脑后。
有时,这一切就好像凤姐的自夸:“我9岁起博览群书,现主要研读经济类书籍和《知音》和《故事会》等人文社科书籍。我20岁达到顶峰,智商前300年后300年无人能及,没有人会超过我,在智力上他们是不可能比我强的,那就在身高和外貌上弥补吧”。凤姐成了一个笑话,因为她没有客观地看待自己,只是一厢情愿地认为自己是一个天才,活在盲目的自我崇拜之中,并硬说自己具备她所没有的才华。
“天才”在现实中往往比“常人”有更多的痛苦,他总是会为常人不纠结的事情而纠结;为常人不焦虑的事情而焦虑;为常人不痛苦的事情而痛苦。他有时也羡慕常人可以有平和的心态,但羡慕的同时,他却忽视了自己无止境的贪婪。
当然,自负与自卑是因果的两极,当他陷入到膨胀之中的时候,也是自卑与自恨登场之时,毕竟他极其敏感,易于受到伤害,他的乌托邦无法经受现实的考量,他完美的形象也无法接受时间的检验——当他不是最优秀的;当别人没有以他为中心;当他不能被所有人尊重的时候,他就会陷入到自卑甚至是自恨之中。
他的成长环境往往过于负面,充满了苛责、否定、束缚、有条件的爱,或他父母本身就是极其自恋,争强好胜的人,在此种环境中长大他无法按照自己原本的样子成长,他必须好像变色龙一般去适应如此的环境;他必须好像战士一般去证明自己的价值;他必须把自己一切“坏”的品质去掉,以取悦身边的人,只有这样他才能生存,只有如此他才能被爱。因此,他比一般的孩子更加勤奋,如此的努力并不是因为他热爱学习或喜欢周围的人,只是因为他的内心充满恐惧。此种焦虑一旦形成就好像一种邪恶的力量,它会逼迫他努力做好一切,不然就好像马上要落入万张深渊,此种焦虑我们可以定义为:基本焦虑。
“基本焦虑”成了他人生的发动机,而非他自己的情感与喜好,因此他总是会陷入到病态的执着之中,毕竟他的人生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活着,而好像被猎狗追赶而不停地奔跑,他停不下来。所以,他必须相信自己是不凡的,他必须做好这一切,就算他做不到,他也会一直做这样的梦。
因此,他的人生是带着“原罪”而来,而他一生都是在“赎罪”。因此,他就不可能对自己真实,不可能对生活真诚。他会把自负当成自信,把骄傲当成能力,把伪装当成品德,因此他自己也成了一个假装的自己。但这种假装让他感觉良好,毕竟这迎合了他内心中的需要,毕竟他需要用假装的强大,并且让自己相信自己已经强大来逃避内心中那个卑微的小孩。所以,他从心里不愿意相信这一切是假的,不愿意看清这个现实,不愿意承认自己仅仅是一头装成马的驴而已,不愿意承认自己依然是原本的那只“丑下鸭"。毕竟,如果他看清了,承认了,识破了这一切的谎言与欺骗,那么他就必须要面对内心最深处的恐惧——成为他自己。
此时,他已经成了”朝鲜运动员“,他在生活中所做的一切都不再是因为自由与热情,而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对他来说喜不喜欢真的是一种奢侈,这个过程也并不重要,他在乎的只有结果。在如此焦虑下,就算他毕业之后也会经常梦到自己又回到考场,而面对试题的时候自己竟然不知道答案,最后他总会惊恐地从梦中醒来。
因此在一些他不确定自己能成功的项目上也许逃避是最好的选择,毕竟不参赛就不会有排名,不努力就不会失败。比如,一位男性患者,只有在“已知”的事情上才会拼命努力,比如他擅长的羽毛球与单机游戏,因为这些他可以确定自己做的很好;看电视和电影他也总是喜欢看自己已经看过的,他套用美剧《绯闻女孩》中的一句台词来说明自己的心理:我希望对未知的世界了如指掌。因为他一直都在逃避未知,因此他的生活总是陷在狭小的圈子里——熟悉的人,多年的女友,擅长的爱好……只有这样他才能逃避失败的可能,只有这样他才能继续维系“别人家的孩子”(从小他就是周围孩子的榜样)的完美形象。凡此种种,他已经禁锢了自己,已经脱离了真实的生活,并继续活在自欺之中。
“只要我们开始追求荣誉,我们就立即不再关心我们自己真正的面目”——卡伦.霍妮
一位患者在信中写道:老师!我突然发现自己追求完美是因为别人!我的生活好像都是别人!不管任何一件事情都与别人的眼光看法及评价有关!我想被别人看的起!我想拥有别人赞许的眼光!我想超越!而且我好像在追求万无一失的幸福!不能受一点伤害!可能自己觉得这样的生活才是我想要的!”
维系 “万无一失的幸福”成了他生活中的头等大事,毕竟这样他才能继续催眠他自己具有超凡的能力。因此,他害怕和异性接触,因为异性会讨厌他;他也害怕当众发言,因为会被人关注;他也害怕别人知道他有病,因为这样就算他治好了,也有一个把柄在别人手中;他也不能年纪轻轻就生病或死掉,因为这破坏了他的掌控感。正如一位患者告诉我,在他内心中他一直认为自己伟大、不凡,应该被所有人看得起,因此他不能接受“理应如此”,诸如,每个人都会死,总会有不喜欢他的人,每个人都会有丢人的时候,都会有意外发生。
因为这个世界没有绝对的成功与幸福,因此他比常人更加痛苦,但他只会责怪“症状”让他不能实现自己的野心,却没有发现自己如此“贪婪”。症状的存在也会成为他不成功的理由——不是我不出色,而是症状的存在才让我失败。所以,他宁愿成为一个病人,也不愿面对自己是一个凡人。
一位患者写道:“王宇老师:我有了一个感悟了,在痛苦中,在挣扎中,我是一个受困的龙,认为未来将会很美好,现在是身不由己,不是我能力不足……当在现实中跨出去了一步,我发现自己是一个无能、可怜、愤怒的人。但我总是在对抗,认为这并不是我,我只是被其所困。所以,我无法体会我所面对的现实,也没有在其中吸取经验,更不敢面对一个这样的自己……”
“受困的龙”成了很多患者陷入症状的隐喻。虽然在现实中他已经一败涂地,头破血流,但如此的自负依然支撑着他,他不敢直面现实中那平凡的自己。因此,他必须在生活中找寻各种支撑,这一切仿佛成了救命稻草,毕竟幻想的破灭就意味着陷入到自恨的深渊。因此,他往往对过去的成就如数家珍,诸如,他高考的时候是县里第一名;他初中的时候是班长;他在竞赛中获过奖;他是成功的商人或政客;他有完美的履历;他有绝对端正的品德……因此,他必定有“一双隐形的翅膀”,注定会飞向远方。
从小,他就和身边的孩子不同,在别人傻傻玩乐的年级,他就已经“志存高远”,就连做梦,也容易做一些和“伟人齐肩”的梦。比如,一位患者告诉我,小的时候他的理想是要当美国总统,而后来得知总统要美国出生才行,因此他后来改换了理想,他要成为美国大学教授,成为可以和上帝对话的人。虽然在现实中他只是一个长相普通的小公务员,但走在大街上或地铁里,他却觉得每一个女孩都向他投来了爱慕的目光,但可悲的是30岁了他依然没有谈过一次恋爱;另一个男孩,虽然他在眼镜店工作,不过他却觉得丢人,他认为自己的“脸”看起来就应该是当官的,这个工作根本就不配自己,虽然他没有啥学历与能力。
为了获得成功,他必然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只有这样才能获得他人的赞许。因此,他做事情往往不是因为喜欢,而是为了证明自己的伟大,因此任何事情他都需要做到尽善尽美。比如,一位男性患者开了一家店,本来他可以让快递帮他送餐,但因为时间无法保证,所以不管多忙,他都要自己送,而且他用的食材,制作的工具都需要是最精良的,这样别人才会给他好评。因为他太过在意别人在他店铺的评价,因此有一个人给了他差评,他竟然冲到对方家里让对方修改过来。而工作中他最怕的就是别人催单或不耐烦的电话,他谈到与其说辛苦,不如说如此的焦虑与压力更让他难以承受。本来他可以不在乎这些细节,但因为他要做到最好,因此他必须逼迫自己在每个细节做到无可挑剔。
为了“万无一失”的成功,他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但过大的压力反倒让他无法正常发挥自己的水平,更容易把事情搞砸。毕竟做事情的意义,对他来说已经不再是做事情本身,而在于卓越的结果,只有卓越的结果可以证明他的不凡。这一切成了无形的压力,让他不堪重负,最后反倒会做不好任何事情。
就好像一些学生,当没有要求自己学好的时候,成绩还说得过去,一旦开始要求自己学好,结果书也看不懂了,老师讲的课也听不进去了。为了做好,他就会逼迫自己集中“百分百的注意力”,结果他的注意力更容易被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所干扰,比如,同学在转笔、地上有纸屑、电脑旁有一盆花或自己会失眠与躯体的不适。一位女性患者告诉我,如果不是这些干扰她的症状,她一定可以考上清华,而不是三本。干扰,成了她不成功的理由,这又维系了她的“自信”——不是她不行,而是她没有发挥出她真正的实力来。
患者有时也会非常固执地“屡败屡战”,此时他的坚持并不是因为喜爱,而仅仅是他不想认输。记得,一位男性患者一直对高中喜欢的女生念念不忘,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追求对方一次,虽然他已经被拒绝了七八次,但他依然不死心,然后会继续“修炼”,再找这个女生尝试。此时,他对这个女生已经不再是爱,而仅仅是一种对成功的执念与自我价值的证明罢了。而另一位男性患者每隔几年就会换一个行业,因为可以做好的事情对他就已经没有吸引力了。对女人也是如此,每隔半年他就会换一个女友,因为他得到了,这个女人对他就没有意义了——毕竟,他所追求的一切,不过是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不过是为了凸显自己的不凡。所以他从来都没有真心爱过,无论是事业,还是女人。
他对赞美的需要是极其强烈的,但越是如此,他就会变得极其敏感,担心别人看不起自己——别人在讲话的时候,他会担心别人在议论自己;别人笑了一下,他就认为别人是在嘲笑他;他也很容易在别人的话或表情里解读出对自己的否定……因此,他非常要面子,自尊心也非常强,无法容忍他人的否定与嘲笑。当别人伤害了他的自尊的时候,他很容易暴怒,但有时顾及情面他也会压抑,所以他总是处理不好和别人的关系。
所以他的“自信”经历不起任何打击,毕竟这一切是来自于成功的堆砌;赞美的积攒;失败的逃避;自我的美化。所以,他并不爱真正的自己,他只爱他身上的光环,无论此种光环来自于想象还是现实。
他并不在乎真实的自己是怎样的,他只在乎自己表现的是否无可挑剔,在别人眼中是否完美无缺,如果这些都做不到,那么他就会活在幻想的世界中拼命地美化他自己。比如,一位在工地上干活的患者,在电焊的时候他无法专注,因为他满脑子想的都是自己是球王贝利,无数双眼睛和镜头在关注着他,他活在欣喜若狂之中;而另一位患者因为想成为歌星,所以在24岁的时候开始学习唱歌,但仅仅是刚开始学习而已,每当他唱歌的时候头脑中就会浮现出来明星的画面,他已经把自己当成了明星。
“想象力在自我理想化的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因此在追求荣誉的整个过程中必然会充满幻想。无论一个人如何为自己讲究实际而感到自豪,无论他在追求成功、胜利、完美的行动中如何确实讲究实际,可是他的想像力无时不在陪伴着他,使他把幻想当成真实的东西。”——卡伦.霍妮
自信与自负最根本的区别在于,一种是来自于现实,一种是来自于想象。为了维系自负,患者最终只能成为一个伪装的,一个自欺的,一个虚假的人。他极其善于自我美化——懦弱会被他美化成品德;幻想会被他当成理想;伪装会被他自诩为正直;讨好会被他解读为善良……
举例来说,一位女性患者被车撞了,但当司机无理辱骂她的时候,她却不反驳,当问她为何不回骂的时候,她谈到:难道你想让我成为一个市井、没文化的女人?其实,她不过是把自己装到了“素质”的套子里,而压抑了自己的情绪。而有时,为了让所有人都说她好,结果她成了一个没有脾气的老好人,只要别人的请求她都会答应,而不懂得拒绝。所以她每天都好像韩剧女主角一般可爱,可亲。她的伪装被她看成是圣洁,她的压抑被她看成是修养,如此的悲剧人生,竟然被她看成比他人更加崇高。其实,她不过是在演戏。
其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种叙事,就好像自传一样,我们是怎样的人,就要看这个自传是如何写。就类似于“胜者王侯败者贼”一样,历史是怎样的,要看记录历史的人。因此,我们往往并不知道真实的历史,只知道“统治者”想让我们看到的“真相”。神经症患者也很好地利用了这一点,毕竟他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反正都是他一个人说的算,就算出现严重的失误,也可以被他粉饰。
所以,他是谁,他怎么样,完全在于他如何操作,白的可以说成黑,黑的也可以漂白。比如,那个执着于高中女同学的患者,虽然他是为了证明自己,而非是真爱,但他却把这一切美化成了一种对爱的执着,在他的眼里自己简直成了情圣;另一个患者当他无法和同学处好关系的时候,他非但没有反省自己的问题,反倒认为是同学太幼稚,没有共同语言,他们素质比较低,把责任都推卸给别人,那么他就没有任何问题了。一位患者在谈论他过去的时候也总是谈到过去多么辉煌,多么成功,是学校的小霸王,一个人和十个人打都不服输。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后他突然告诉我:王老师,你有没有注意到我只和你说了我打别人的光辉事迹,却忽略了我被人打的事?
有时,就算事实摆在眼前,他也可以把一切责怪到他人不好,环境不好,中国人不好,似乎他脱离了中国,中国人,移民到别的国家,一切都会好起来。当一位男性患者大谈中国人的劣根性,女性的拜金,中国对言论自由的限制,他是如何向往美国民主国家的自由,民风纯朴的时候,我提醒他是否把自己的失败都推卸到了外在,而不愿承认自己的不足。毕竟,在现实中他没有他自己所期望的明星般的外貌,别人也没有把他当成伟人一样的尊重,女人也不曾把他当情圣来膜拜,为了逃避现实对他自负的打击,他躲到了一个人的世界之中,不交朋友,也不谈对象,并把责任推卸给了外界,而不是归结为他自身,这样他就可继续在幻想中维系骄傲了。
神经的自负和真正的自信并不是量的区别,而是质的不同。如果他原本的“自信”真的牢固,也不会如此轻易地被打破——毕竟他的自信是建立的幻想之上,是没有根基的树。比如,对于真正的骑士来说,他的自信来自于出众的剑术及良好的品德,但对于“唐吉诃德”来说,这一切都仅仅来自于想象——他幻想自己是一个骑士,马上他就具备了行侠仗义的本事。自信来自于能力,而自负是硬说自己具备想象中的能力与品德。
自负与自卑是因果的两极,当他陷入到膨胀之中的时候,也是自卑与自恨登场之时,他的乌托邦无法经受现实的考量,他完美的形象也无法接受时间的检验——当他不是最优秀的;当别人没有以他为中心;当他不能被所有人尊重的时候,他就会陷入到自卑甚至是自恨之中。他恨自己不能如自己所认为的那般无所不能。
本文系作者 @河马 原创发布在河马博客站点。未经许可,禁止转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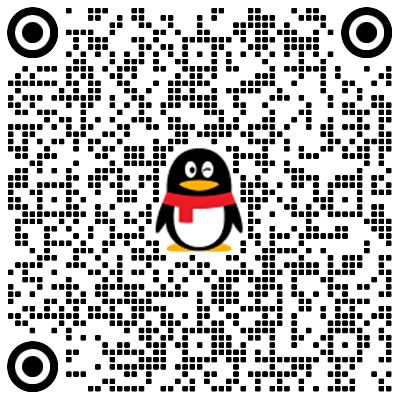
暂无评论数据